刀郎的创作,可分为新疆和后新疆两个时期,分界线是2009年,这个时间节点所带来的影响,对刀郎来说巨大到让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刀郎十年后才发表新作品,这期间的波澜起伏外人无从得知,而新专辑的主题和表达证明刀郎有了新的创作立场,并且绝无可能再回到以前。《弹词话本》直截了当地展示了刀郎的转变,用一张和新疆毫无瓜葛的专辑,出人意料地踏进了一个他似乎不可能进入的领域,正当人们错愕、猜测之际,仅隔半年,刀郎又推出《世间的每个人》,新疆回来了,但回来的已不是彼时的新疆。涅槃般的刀郎轰然耸立在人们面前,陌生而高不可攀,面对新作品,人们既兴奋又沮丧,掌声渐次响起,一圈一圈蔓延开去,无论理解不理解、喜欢不喜欢,人们知道,中国流行音乐创作已经被改写了。
谈论《世间的每个人》有不小的难度,因其内容的深邃和复杂远超想象,谈论者便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主观判断的色彩,这种主观性会是《弹词话本》的数倍。《世间的每个人》注定将充满争议,不是争议它的水准,它的超高水准是不存在争议的,是毋庸置疑的,争议的是《世间的每个人》从整体到具体作品的不同理解,这样的争议是良性的,大量杰出的艺术作品都遭受过争议。
遗憾的是,争议尚未发生。在艺术批评的链条中,流行音乐处在很末端的位置上,大部分时候,流行音乐在学界的视野之外,原因很简单,流行音乐的商业性、流行性、工业生产等特征无法吸引学界资源介入,绝大部分的流行音乐作品都不需要艺术批评参与,同时,艺术批评家当中对音乐性具备既敏感又有专业判断能力的人也是少数。而现在,刀郎几张新专辑的面世,让事情发生了变化。纵观全球流行音乐界,能入艺术批评家法眼的歌手也不多,鲍勃迪伦、平克弗洛伊德、U2、乔治迈克尔几位应该榜上有名,他们得到批评家的青睐,得益于上世纪后半段泛滥全球的左倾意识形态思潮,这股思潮势力强劲,国内也深受其影响。刀郎的新作品是超越意识形态的,这些新作品对理论的要求既古典又现代、既简单又复杂,这增加了难度。但越是这样,刀郎新作品越需要高质量的严肃评论,刀郎硬生生把国内流行音乐的创作拔高到了想象不到的层面,评论不能缺席,学界对刀郎作品认真研究和评述,是刀郎应得的礼遇。
当然,现在情况还不太乐观,刀郎以一己之力让严肃的、大众的两头都处在惊愕之中,不知该如何面对他的新作品,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我仅仅是业余爱好者,不是专业人士,但我是刀郎新作品最坚定的支持者和鼓吹者。虽然我也一直处在惊愕之中,但我想谈论《世间的每个人》的意愿是如此强烈,顾不上粗陋,也无任何理论可言,我只想说出关于作品既直观又主观的那些感受。
面对《世间的每个人》,第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便是这张专辑在表达什么?不同于主题较为明晰的《弹词话本》,刀郎在《世间的每个人》里想表述的东西似乎十分隐晦,听众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拨开繁枝蔓叶,寻找《世间的每个人》主题,是解读这张新专辑的首要工作。刀郎在探讨什么?我的答案是,《世间的每个人》瞄准的不是具体的生活,而是抽象的生命,不再是《西海情歌》,而是《我的星座》,这张专辑欣赏时的难点便是这样产生的,《世间的每个人》呈现了刀郎关于生命一些抽象的、形而上的、普世的观点和思考。而生命这个概念过于恢宏和空泛,刀郎选取了命运主题力图承载他的思考,但命运依然是抽象的,必须再分解到更具体的概念上,然后有了宿命、死亡、告别这些主题。所以《世间的每个人》的主题是立体的,是这样一种有层次的结构:生命——命运——宿命、死亡、告别,继而形成了《世间的每个人》的丰满和深邃。
死亡在专辑作品里比较容易察觉到,宿命需要用点心就能体味到,告别可能隐埋得比较深,但告别却是刀郎在专辑里最想表达的主题。这张专辑最初的名字叫《新疆往事》,尽管最后专辑放弃了这个名字(我认为放弃得对),但恰恰是这个被弃用的名字给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和提示。刀郎的初心为什么在往事上?人们什么时候会提出往事这个词语?我们告别了某些事情,或行将告别某些事情,一般便会将之称为往事。刀郎不惜事先事先说出新专辑的名字是《新疆往事》,透露了刀郎表达告别的愿望是多么强烈,这是关乎新疆的告别,这也是超越新疆的告别,哪怕大部分歌曲并无告别的内容,告别依然是整张专辑的基调,告别就像花粉,洒满专辑的里里外外,听久了,便在你的内心生出芽,不同的人在心里体会它不同的形状。世事就是如此,有些东西会从你的生活里离开,但不会从你的生命中离开。告别不是解脱,也不是了断,告别时不一定郁郁寡欢,告别后也不一定一马平川,告别更像封存,既是滋养,也是侵蚀。
所以,在我看来,《世间的每个人》首先是刀郎一个声势浩大的告别宣言,这里的“声势浩大”是指我内心的感受,事实上在专辑里刀郎告别的意味是隐藏的、是被遮蔽的。但大多数人在新专辑面前至少都不会反对这样一个看法:出现了两个刀郎,一个新刀郎,一个旧刀郎。推前一步,刀郎毫不掩饰地向我们表明:告别旧刀郎,诞生新刀郎,不管我们有没有准备好。而整张专辑里,我认为最与告别有关联的是《向着大海而行》。
与隐秘的告别主题不同,死亡和宿命两个主题较易被听众感受到。宿命是藏在歌词下面,但藏得很浅,略微用心便能察觉到。而死亡主题,刀郎是直接正面面对的,没有任何掩饰。让人感兴趣的是刀郎对死亡主题的处理。死亡是古今中外艺术作品里一个永恒的主题,汉文明自然也有一个长期形成的关于死亡定义与概念的传统,这个僵硬的传统集中了汉文明对死亡的认知和表达。而刀郎的处理,是新颖的,是对传统观念的解构。在刀郎的死亡主题里,死亡与恐惧无关,与哭天喊地无关,与失去无关,死亡是非罪的(可能会有朋友提到《南门》,但《南门》的主题不是死亡),死亡不是一个硬币有两面,死亡是个球形有无穷多的面,死亡自然不是终结,死亡是生命中的应有之义,我们应该害怕死亡吗?不,不必害怕,请听《我的星座》,而犹如神曲般的《奇台三十里》更是颠覆性展现了刀郎对死亡的看法。
像这样去搜寻《世间的每个人》的主题而得出的结论未必能服众,权当主观的、十分个人化的一些观点。下面选取《世间的每个人》里几首歌曲解读一下,当然,它们依然是主观色彩浓厚的个人判断。
《世间的每个人》。这首专辑同名歌曲放在第一首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释放的与其说是信号,不如说是气场。《世间的每个人》可能是整张唱片里最不易理解的歌曲,尽管它有着令人沉迷的旋律。专辑里,它的语言最质朴,它每一句歌词、每一个细节都是具象的、具体的,但却最难理解。一个形而上的刀郎跃然纸上。它似乎与一切都有关,又似乎仅仅是刀郎的自说自话,它弥漫着刀郎的个人经验,它加总了众多栩栩如生的细节,最终却指向了一个抽象的世界。它是一种生命状态的描述,带来的感受飘忽不定、难以言说。这首歌的魅力无法阻挡,爱上它不可避免。
《我的星座》。这是一封独一无二的遗书,这是罕见的、事先张扬的精神遗书,这是死亡甚至像祝福的遗书,这是一封高贵的遗书。歌曲里,刀郎放下了全世界,却不放过自己,这种真诚的苛刻有着老派的优雅。一切世俗的琐碎都被刀郎扫在了门外,他只关心尊严,而这尊严必须有来源、可传承,有年少也有无垠。这封没有任何悲戚之情的遗书,虚晃了众人的双眼,这是一封保质期可长达百年的遗书。
《向着大海而行》。刀郎的告别宣言。这是告别进行时,人在征途,大海是目标,出发地被刀郎刻意模糊了,一个场景转一个场景流露的都是崎岖不平,即便目的地大海也不总是鲜花盛开,死亡若隐若现。尽管有许多象征意味浓郁的写作手法,这首歌表露出来的坚强还是让人印象深刻。很多人怀念刀郎的呐喊、高亢,但呐喊与高亢未见得就是坚强,《向着大海而行》这样沉稳叙述、语气坚定才是真正的坚强。进行曲风格的旋律让这首歌成为专辑里最易学唱的歌曲,但哪怕旋律再高昂向前、节奏再铿锵有力,刀郎那强作欢颜的乐观仍然能被人捕捉到。没错,此时的告别是迫不得已的,那给世人看见的阔步,那些繁花迷眼的意象,那远在千万里之外的大海,注定陌生。
《南门》。我已然能想象到未来的某个时刻,数万人现场合唱《南门》的壮观景象。上天,请赐予我们所有人勇气,当需要勇敢的时候不再畏缩,不要让刀郎独自一人。
《奇台三十里》。本张专辑里创作成就最高的作品。这是一个看上去完全没法用流行音乐进行创作的题材,刀郎神奇地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后发布的作品趋于完美。一个中国乡村的葬礼,在音乐形式的呈现上有很多种选择,但谁会想到采用布鲁斯风格?刀郎这个天才般的运用真是妙不可言,这是《奇台三十里》最合适、最匹配的音乐形式,音乐完成度无可指责。刀郎提供了一个本土蓝调的范例,是对流行乐坛的开创式贡献。刀郎左手布鲁斯,右手却是利刃,这利刃的功能出乎意料,这把温柔牌利刃,先是剔除了哀伤,然后召回天堂,进而解构了传统的死亡认知,于是墓园是祖传的,死亡是轻盈的,神仙是可见的,村民是漠然的,葬礼似乎是个无声的舞台剧,连最凄厉的唢呐你也听不到它的声音,这和你见过的任何一场农村葬礼都不相像,但你明白这跌跌撞撞的轻快并不真实,终于,当听到“命中注定在这荒芜湖畔干涸家园”,当听到刀郎那沙哑的尾音的时候,你的眼泪再也无法忍住,那利刃的最后一击,直刺宿命的中心,歌曲主人公的一生都亮晃晃地摊在了我们面前,死亡和宿命相生相伴,死亡一点都不可怕,它就像午后睡去一样,但宿命的摆脱却遥不可及。刀郎没完没了地唱着“一年又一年”,就像这最后一刺扎得太深了,鲜血流不完、滴不尽。
《风向朝西》。新疆风情画。虽然它有着夏加尔风情绘画作品的那般诗意,但却没有夏加尔作品里的梦幻。相反,《风向朝西》令人不安。这首歌是专辑里涉及新疆元素最多的一首歌,有些词语大部分人可能是第一次听到,比如“麻扎”,维语里是“墓地”的意思。不过,这些都不影响大家对这首歌的喜爱,《风向朝西》或许是专辑里最受欢迎的作品,因为它太好听了,情绪太饱满了,诗意太迷人了,但不要试图在假线性叙事的歌词内部找到逻辑关联。《风向朝西》短短几百字,精炼出的新疆味道十分准确、感人,它的每一句歌词都可独立成篇,它与观光意义上的新疆风情不一样,它有最纯粹的爱和最不屈的挣扎,它是匍匐在大地上最普通那群人的风情,它是残破、贫寒的风情,它是被践踏后依然徒劳地追逐生命完整的风情,它是让人泪流满面的风情,它要在如粉末般飘起又沉下而无人在意的寻常日子里,加进惊心动魄,它费尽所有力气让卑微和神圣之间的上升通道不要关闭,它是另一种人们会哽咽的风情万种,它让人们去理解真正的新疆。
《梦更真实》。《南门》的姐妹篇,一首真正的挽歌。如果说《南门》的哀悼有多么痛彻心扉,《梦更真实》的挽歌就有多么令人绝望。动听的旋律和宜人的节奏是它华丽外衣,它想拼命裹住的是七月后凋零的王国。晦涩的隐喻,盖住了刀郎对新疆最深沉的情感,那么优美、感性的旋律,却嵌入了许多理性、拗口的语句,刀郎内心的悲伤是多么不可言说啊。更让人泪目的是,刀郎的悲伤最终发展成了绝望,我相信他宁愿自己大错特错,也不愿“上锁的孤岛”预言成真!这首歌的核就是那句锥心之痛的“我的王国开始凋零”,尽管它在副歌里,尽管刀郎使用了变音,但这句歌词是《梦更真实》的创作原点,如此伤痛的原点,却最终抵达了更加伤痛的句点,从王国到孤岛,这绝望的旅程啊,要如何回望绝望的异乡?
2021-1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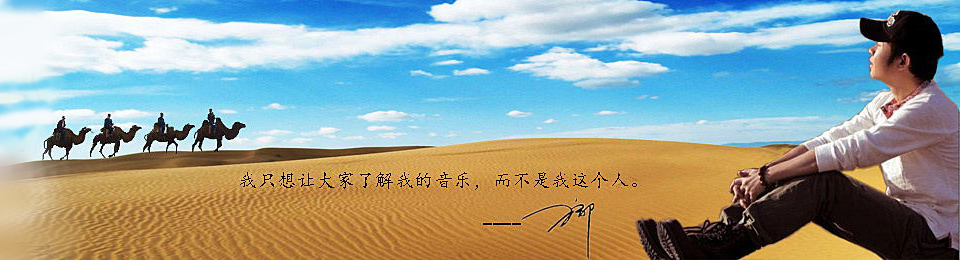


我要评论